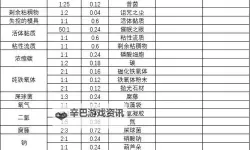转过去腿趴好准备打直肠针:医院夜色中的自我对话
夜色像厚厚的毯子盖在医院走廊,安静到能听见心跳。我把身体转过去趴下,胸贴床垫,臀部抬起,膝盖微弯。护士进来时,呼吸声在胸腔里扩散,像风铃在轻响。我对自己说: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检查。
肚皮贴着冷凉的床单,皮肤的温度从背脊扩散。我把注意力放在鼻腔缓慢的气息,像在听见一个老朋友的低语。心跳与仪器的滴答不成对,仿佛两种世界在同一个房间对话。我问自己:在黑夜里,身体会不会把脆弱暴露得清晰?答案藏在呼吸里。
医生走到床边,手套的味道很重,声音更近。她示意我侧身,把一条腿拉向胸前,另一条伸直,脚背放在床沿。墙上的钟表滴答不休,像在数我的勇气。此刻针头在灯光里发出冷光,心里对自己说:别怕,给身体一个信号,让疼痛成为记忆的碎片。
走廊的灯光像细线,穿过纱帘投在地板上。窗外是城市的夜,远处车声混成一场无声合唱。我把呼吸放缓,想象胸腔里有一条安静的河,流过胸壁、腹部,抵达需要关照的地方。此时的自我像旁观者,记录这场安慰与告别的仪式。

针头的尖端接触皮肤的那一刻,冷意从表皮蔓延到肌肉。医生的口吻温和,动作熟练,像在推进一段已写好的剧本。肌肉收缩,呼吸短促,我把意念拉回胸口,脚趾紧抓床边。疼痛没有想象中猛烈,更多是一段短促的波动,随后归于平缓。
针刺结束,皮肤还略酸痛,夜雨停在屋檐的感觉慢慢退去,像夜色重新清澈。床单的味道变得熟悉,带着消毒液的清凉。护士收起器械,拍拍我的肩膀,仿佛在说无声的肯定。我因此感到稳当,脚步里多了一分踏实。
夜深房间里,我继续与自己对话。身体的边界在这座城的夜色里被推拽,提醒我仍活着,仍有选择。也许明天还有新检查,新的不安,可我愿把脆弱收起来,放在心底的角落,准备迎接未来的日子。